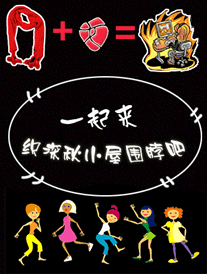【 2005-01-04 23:17:11 编辑:深秋小屋 字体: 大|中|小】

1990年4月,
在去敦煌的路上,三毛百感交集--
大西北苍苍茫茫,天高地宽,唤起了她往昔在撒哈拉大沙漠时期的情感。
一股浓浓的乡愁。
她开始了另一种爱情--对于大西北裸露的土地,那片没有花朵的莽莽荒原的挚爱。
……
她把东西全部丢在车子的座位上,像听到了生命的召唤,不由自主地向没有绿意的荒原跑- -狂奔过去。
荒漠的一望无际的西北高原上,吹着坦坦荡荡的野风,卷裹着三毛那略显单薄的身体……三 毛一阵阵惊喜。
在《夜半逾城--敦煌记》中,她忘情地写道:
在接近零度的空气里,生命又开始了它的悸动,灵魂苏醒的滋味,接近喜极而泣,又想尖 叫起来。
很多年了,自从离开了撒哈拉沙漠之后,不再感觉自己是一个大地的孩子,苍天的子民。 很多人对我说:"心嘛,住在挤挤的台北市,心宽就好了呀。"我说:"没有这种功力,对 不起。"
三毛站在万里长城的城墙上,别人都在兴致勃勃地看墙--古老斑驳、甚至有些残损的墙, 她却仰头望天,自言自语道:
"天地宽宽大大,厚厚实实地将我接纳……"
一阵荒原的朔风,强劲地吹了过来。三毛觉得很惬意,她说:
"很快乐……吹掉了心中所有的捆绑。"
在去敦煌路上,三毛认识了一个同车的在莫高窟工作的旅伴,一个名字叫"伟文"的年轻 人。这位叫"伟文"的年轻人,长年在莫高窟临摹壁画,他不仅是三毛的热情读者,三毛还觉得 她与他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缘。
在敦煌夜晚人影稀少的街头,三毛与伟文完全沉默地在大街小巷走着。三毛写道:
……风,在这个无声的城市里流浪。夜是如此的荒凉,我好似正被刀片轻轻割着,一刀一 刀带些微疼地划过心头,我知道这开始了另一种爱情--对于大西北的土地;这片没有花朵 的荒原。
在去敦煌的一路之上,三毛并不很在意车子经过了什么地方又到了什么地方。但有一个地方 最让她心动,甚至一夜都"没有阖过眼"。三毛写道:
……只是在兰州飘雪的深夜里看到黄河的时候,心里喊了她一声"母亲"。
三毛希望能在莫高窟的一个洞穴里,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呆上一会儿,那个叫"伟文"的年轻 人,帮她实现了这个愿望。
在《夜半逾城--敦煌记》中,三毛真真切切地写道:
在我们往敦煌市东南方鸣沙山东面断崖上的莫高窟开去时,我悄悄对伟文说:"你得帮我了 ,伟文,你是敦煌研究所的人。待会儿,我要一个人进洞子,我要安安静静地留在洞子里, 并不敢指定要哪几个窟。我只求你把我跟参观的人隔开,我没有功力混在人群里面对壁画和 彩塑,还没有完全走到这一步。求求你了--。"
"今天,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我又说。
当那莫高窟连绵的洞穴出现在车窗玻璃上时,一阵眼热,哭了。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 沪ICP备11026210号-1
版权所有 ©深秋小屋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13154293@qq.com ladyscn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