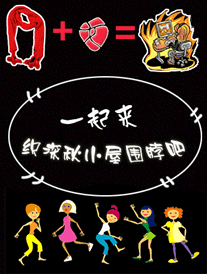中国同性恋 数字及其他
【 2004-08-18 23:58:00 编辑:凡 柔 字体: 大|中|小】
[这篇文字所展示的观点,在向我们传达着一个信息就是面对压力,无论是传统的还是自我的,来自社会越来越广泛的理解的背後该是我们(作为拉拉)整理自我内心的时刻了,作为拉拉是不是要结婚而不是不该结婚......] 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目前官方没有关于同性恋发生的数据和一般性取向者的对照数字,但学界估测国内同性恋者约有4000万人。这意味着,我们身边每一百人中就有两到三人或更多的人像小K一样,愿意选择同性为伴侣。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生活方式渐次走向公开 虽然不穿奇装异服,说话也没有怪腔怪调,但一些同性恋者还是会被身边细心的人发现。“如果有人问到这个问题,我会坦白地告诉他,我是同性恋。实际上出于尊重的角度,很少会有人直白地问我是不是同性恋,就好像谁也不会突然去问一个人是不是异性恋一样。”27岁的小江 和都市里许多年轻人一样,毕业后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闲暇时经常上网、泡吧。略显不同的是,他是一位同性恋者。 在一家公司做网络设计的w说:“父母和身边的朋友早就知道我的情况,他们都很理解我。母亲曾对我说,无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只要做个好人就行。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很坦然。” 据了解,许多同性恋者在知道自己的性取向之初,都会感到迷茫、不知所措。w也是如此。他从小就喜欢跟男孩子在一起,而对周围的女孩一点儿也不感“兴趣”。随着慢慢长大,他懵懂地意识到自己“不对劲”,又非常害怕别人知道,就一直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 “读高中一年级时,这件事让我变得非常烦躁,只想跟家人说明白。我想到买一本介绍相关知识的书给他们看是最好不过的方法。”而在十几年前,市面上极少能见到同性恋方面的书籍,16岁的w逛了很多书店,好不容易买到一本,其中一页提到了同性恋现象。回到家,他把这“宝贵”的一页折起来,又费尽心思把它放在一个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地方。 他 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看到书自然明白w要对他们表达什么,在诧异、不解过后,他们终于接受了现实。 在w的故事过去十几年后的今天,“同性恋”这个原本陌生的词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一些同性恋者也不介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特殊身份”。在许多大城市,还出现了同性恋者交流的公共场所――比如酒吧和同性恋网站。 一位公务员和几位朋友偶然进入了一间同性恋酒吧,他说“感觉有些不舒服,但仔细一想这是人家的私生活,与外人无关。” 婚姻,成为最难逾越的障碍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丛中说,在中国,不少人觉得同性恋不道德,实际上这是人们的认识不足。据有关调查显示:同性恋者分布于社会的各个层面,不因社会地位高低、地域大小而有所区别,除了性取向不同以外,与一般人群并无差异。 人们的误解可以逐渐消除,倒是另一个问题,令长期致力于同性恋相关研究的卫生部艾滋病咨询专家委员会政策组成员、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深感忧虑[B]:“在4000万左右的同性恋者当中,约有8成迫于传统和社会的压力,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婚姻。这个边缘化人群带来的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B]张教授这种观点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是: [B]在中国,约有3000多万名同性恋者已经或打算违背自己的意志,选择与自己并不爱的异性结婚、生子。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配偶对此一无所知。那么,这样的婚姻意味着什么? [/B] 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与普通人相比,同性恋者更容易陷入焦虑和无助。因为尽管外界对同性恋现象给予越来越多的包容,但来自传统社会的种种压力对他们的生存、生活方式还是施加着不可抗拒的影响。许多同性恋者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不愿提及婚事,成为亲朋好友眼中的“老大难”;有些为避免招惹“麻烦”,干脆草率成婚。 一位32岁的男同性恋者被父母逼着结婚,可他又十分不情愿。最后他问张北川教授:“我找一个拉拉结婚行吗?” 张教授说:“拉拉,就是女同性恋者。现实生活中,很多同性恋者想找一位异性的同性恋结成没有实质的婚姻,开始双重生活,以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关于这个问题,没有标准而正确的答案。我告诉他,这是一种不道德的选择,对社会、对家庭、对他人来说都不负责。为此,希望他慎重考虑。”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 沪ICP备11026210号-1
版权所有 ©深秋小屋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13154293@qq.com ladyscn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