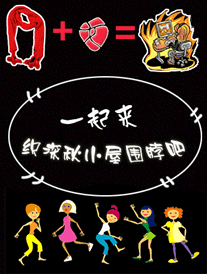上海往事(写在前面)
【 2003-06-01 00:00:00 编辑:美丽心灵 字体: 大|中|小】
先谢谢大家。
花了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完成了一个8万字的小说,很有成就感。
之前我曾动笔写的另外一个长篇到至今已一年多了还只有写了4万多字。所以,“上海往事”能写完完全是大家的热情和鼓励,如果有一天出版,我会在书上写明:
送给一群充满阳光欢笑和智慧的女孩子,送给她们的“笑语扬眉”。
这是一个忧伤无奈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有我和我的朋友们的影子和心迹,甚至也许有素不相识的你的一些偶合的境遇。
其实,我想写的,就是一个时刻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和两个可能就走在我们身边的人。
很多人认为同志小说总在忧郁气氛中开场和结束,我只能说,对于这一部,我很遗憾,因为一开始已经定下了一个忧郁的基调和一个可能消失的生命的伏笔。
我希望,下一部,我写的是喜剧,给更多的只论爱情不论性别的人们一些希望和鼓励。
另外,我不强调“同志小说”这一提法,也就是我一贯认为的,同性和异性的恋爱在本质上应该是一样的。即使这个故事,我也完全可以把她们其中的一个写成是男孩子。
只要真心,就能相爱。
很久以前,我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不相信爱情的人了。但是来到这里,经历了不少的人与事,包括写作,包括大家的评论,我发现自己,重新又变成了一个相信爱情的人。
好了,不说了,说多了有煽情加作秀的嫌疑了。
以上,算这部小说网络版的“前言”。
(引子)
那天下午天气很好。我正在厨房里炖一锅鸡汤。电话铃响了。
电话是Anita打来的,说是天气那么好,不想辜负了,不如一起喝个咖啡,聊聊天。我说我正在炉子上炖鸡汤,要不你开车过来吧?我新装修了书房,可以有一屋子的阳光供我们享受。
挂了电话我便开始整理。没多久门铃就响了。
Anita和我同龄,都已经三十出头了。她的大儿子在上幼儿园,小女儿也会说话了。他们家过着很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式生活:男主人是一家企业的主管,她自己在家相夫教子。他们拥有一栋漂亮的小洋楼,两个可爱的孩子以及一条小京巴狗戴比。
这会儿,Anita还没有进门,戴比已经迫不及待地闯了进来。
我想周围的很多人都会象我一样羡慕她的日子,保养得好得不能再好的身材和面容,每天坚持户外运动,平时参加插花班钢琴班舞蹈班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做一手好菜,相夫教子。一切的一切都显着成熟女人的优雅和风情。
说来奇怪,虽然我们并不是非常亲密的朋友--我是个单身女人,对已婚女人有些"理性歧视",认为她们围着男人孩子锅碗瓢盆转很是没有出息。但Anita似乎总喜欢来和我一起谈谈天。她说,和结了婚的女人聊天会让自己觉得世界很小,和单身的女人聊天,世界似乎可以变大一点。
我把Anita领进书房,顺手将写了一半的毕业论文从小圆桌上搬走。
她今天穿了一件浅绿色的薄毛衣,施着淡淡的脂粉。我一直以为东方人用玫瑰色的唇膏会很俗气,但在她那里,却是一种妩媚。
我竟然在阳光下看得有些发呆,她朝我嫣然一笑,轻轻地说,这儿真好。有时候觉得一个人的世界真安静自由。
我把咖啡递给她,笑着说,如果我跟你换,你大概不会愿意放弃阔太太的生活来过这种念书的清苦日子。
那也未必,她说,只要有相爱的人陪伴。
说这话的时候,她笑得温柔极了。我虽是个百分之一百的异性恋者,但也忍不住心头一跳。我想,这样的女人,大概没有男人不会为她动心的。
我们坐在那里东拉西扯了一会,她突然说,阿三,我想求你一件事情。
看着她一脸的诚恳,我说,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吧。
我想让你帮我写个故事。
写故事?我问。
是阿。这个故事我一直想写,都想了很多年了。
我一下子好奇起来:真的?那一定是非常有趣的。
她又一笑。说,也许对很多人来说这很平常。可是对我,当然是一生中最感人的故事。
后来,她就开始讲她的故事。
她整整讲了一个下午,咖啡渐渐凉了又续,日头慢慢偏了西。在日落的最后一瞬,她收住了话题,而我,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Anita走了以后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个故事。我发现我充满了想把这个故事讲出来的欲望。
于是我在电脑前整整抽了一小时的烟,然后打下了"上海往事"四个字。后来的两天我都在半昏迷半亢奋的状态下敲打着键盘。我无法使自己停止。我拔掉了电话线,也不做饭。饿了就把那锅鸡汤在微波炉里转一下喝了。
两天后我终于写完了:一个叫Anita的女孩和一个叫梅蕊的女孩的故事。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把故事的主人公Anita改成了"我",而间或一些我的插话,便是"阿三有问"。
故事从十年前的上海讲起。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 沪ICP备11026210号-1
版权所有 ©深秋小屋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13154293@qq.com ladyscn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