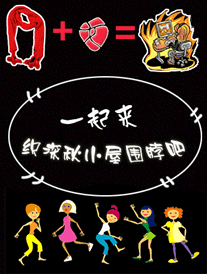走过泉州
【 2003-06-15 00:00:00 编辑:chielle 字体: 大|中|小】
chielle@21cn.com QQ:21327530
走过泉州
早晨醒来,不过八点半。
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书,有点烦。拨号上网,给朋友发了几封无关痛痒的E-mail,又懒怠与人聊天,那些话现在似乎显得干燥乏味,此时勾不起我丝毫兴趣。突然决定出去走走。先去泉州,再到湄洲岛。
给车站售票处打了预购电话,匆匆洗漱完毕,准备了简单的行囊,时间还充裕,便悠哉悠哉地漫步到车站。
这是个突然的决定。
路上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我已有些麻木。终于驶入市区,十多年前的记忆重温,熟悉而陌生。残缺的片段断断续续掠过,除了东西两塔的影子趋近于清晰,基本上淡却了当年的味道。
泉州话与chielle所在城市的方言虽然有些许不同,似乎鼻音重了些,但大体上还是一样的,毕竟同属于闽南语系,彼此的咬音腔调仔细点也能听得明白的。
泉州的街道很窄,巷子多,除非是新开发的城区,否则难得见一条四车道的路。交通秩序显得混乱不堪。行人、单车、人力车、机动车,你拥我挤,好象鬼子进村来了。步行街也远不如厦门利索,显得拖沓异常。可能跟交警的好脾气有关。
我一向不大会走路。走在大街上,常常自顾自地瞎想,不晓得观前顾后,平白无故的也会与人相撞。在这儿,更是晕头转向,左躲右闪,像只喝醉酒的鱼,迷顿在浑浊的海里。
在老城区,房子多是两三层的,很陈旧古老的那种。特别喜欢石雕的墙面,有些磨损,或者散布有裂痕,长着青苔,绿茸茸的。下面是枣红的砖墙,色泽在时间的流淌中退淡去,留下的是曾经的浮华、现今的感伤。木质的窗棱,已蜕变为灰褐色,那是历史记载下的沧桑。窗台上摆着一两盆瘦小的植物,黑色的背景撒上几点新绿,相互映衬,仿佛足不出户的小家碧玉。
店铺极多,可见当地人的生意经念得不错。但从他们的衣着看,品位并不怎样。总能看见一群一群服饰相似或相同的孩子。只会相互模仿,因此丧失了自我个性。
有些老字号,当年的石坊还在,但却已改头换面,做起别的买卖。物在人亡的意境尤为深长。也许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维持长久的。
去了趟古玩市场。
明知那儿的所谓古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假的,但想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又何必在乎真假呢。
器皿、配饰、字画、摆物等等,倒是没什么新奇能让我中意的,结果掏回一大摞连环画(小人书)。家中原本就收藏了不少,但有许多残缺不成套的,时常惋惜。这回便凭着印象将那些没有的买来,不亦乐乎。
一眼便喜欢上路边的刺桐树。这个时节花虽未争荣,但一朵朵的红微微点缀着高大的枝干,衬着这一年细密鲜绿的叶子,雕饰了古城泉州的凄艳。有点儿像木棉树,但花朵比它精致许多。
在开元寺内。
古木参天,清凉幽静,一派佛门净地。
大殿两侧的东西石塔可算是泉州的标志性建筑了。
“镇国”、“仁寿”两塔对望一千多年,彼此凭空敬畏,历经风雨侵袭、地震摇撼,仍威威仪仪显驰骋。
我把身子贴在锈迹累累的铁门上。除了塔外射入的淡微光线,几乎是漆黑的。只能隐约看见斑驳的石壁和小尊的佛像,有厚重的尘土气息和阴森的潮气。
铁门将内外隔绝,旁人无法窥探塔心的一切。禁锢的灵魂会游离躯体。
在古船陈列馆里,看到了1974年出土的泉州湾后渚海船。
曾经远洋的木帆船,在岁月的洗礼中被遗弃,湮埋于淤泥的污秽中。沉默,并不一定是对屈辱的低头,有时则是渴望重新闪耀的征兆。
清净寺是必去的。
对宗教有着特殊的喜好,自知尘缘缠身,难以了断,终归是个世俗的槛外人,但相信冥冥中生与灭的连横,神灵自明,必然度我。
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壹零零玖年),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座具有浓厚阿拉伯建筑风格的伊斯兰教寺。
它处在闹市中心涂门街中段,坐北朝南,门前的石板路看似新铺设的,喧嚣中保持独自的清宁。其中的许多楼宇已不复存在,所剩的主要有大门楼、奉天坛和明善堂。
大门楼用辉绿岩石砌筑,为圆形弯尖顶拱门。楼顶是平台,四面环筑“回”字形的垛子,单看上部,像长城的烽火台。但你绝不会将它与硝烟炮火联系在一起,它是平和的。站在下边,恍惚当心会突如其来地坍塌,将我湮埋在岁月流痕中。
原以为穆斯林习惯于露天的礼拜,这样显然更直接。后来才知道奉天坛的屋盖本是有的,在明朝年间倒塌,没有修复,就不再使用,祭奠搬到新建的明善堂。时光是肩负不起那样的重荷的。现在的坛看起来,相似于马雅文明遗址的某个建筑,一根根石柱林立,又像鲤城区浮桥笋浯村的生殖崇拜物----石笋。殿内四周的空地上花岗岩的残础隐约在草丛中,背负着辛酸与惨淡。
临近傍晚,搭乘公交车到清源山。
平日里是极怕长跑的,但却不排斥对爬山的喜爱。能够感受到犹如生命轮回的神妙。
不算崎岖的山路,已没有多少人迹,有时整段石阶上前后望不见半个影子。听到的,是林中诡秘的幽鸣。四围,满眼的翠绿炫耀着勃勃生机。沉浸其中,很容易抛开心中的阴霾,寂寞的难耐。
别人下山我上山。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偶然碰面,擦肩而过,互相投以一个友好、鼓励的微笑,或者一声亲切的招呼。同样是匆匆过客,他山他水巧相逢,算是缘份。但知道不可能再相见,无意间的邂逅只是留下模糊的面孔,很快就会忘却。
爬山确实很累。清幽的山林中隐约着初夏的燥热。纵然飘着微微细雨,但没走多大段,衣服已是湿透了。将裤脚卷到膝盖上,作用不大,反倒对腿有些压抑。只因是女孩,否则真想打赤膊,管他形象损了多少。
其实山中的景致与别处相比,并无什么较为独特之处。一样的山石,一样的树木,一样的亭阁,但去得并不后悔。因为始终偏爱山中的清泉。小股的水瀑缓缓地从石缝间泻下,极清澈明亮,像轻柔的透明丝缎,抚摩着山的肌肤,又像山的眼睛,赋予其干净的灵气。平静的心能够感受到它平静的流淌。
爬了一个多小时的山,忽上忽下,多是有石板铺设的。沿着标志指示,路过一个个景点,并不想作太久的停留。一再地重复相似的东西,会渐渐失去慧根,想保存印象中的灵秀。
在山上绕了好大一圈,终究是在累得迷糊中回到了山下。仿佛无尽生命的突然夭折,有的,或许是惆怅不甘的遗憾,或许是倦怠解脱的喜悦。
最后去的是老君岩。
平地上,硕大一块石像,七分天然三分人工。憨态可掬,掩隐在绿树青草中。风雨的雕蚀与洗礼,使它具有一股超脱的生气。
晚上,在铜佛寺的环湖小吃摊品尝当地的风味。
有那种一个一个的鱼丸、切成小块的土豆或芋头、长溜溜的豆皮串成的串,还有蔬菜的。用沸水烫熟了,再拌上辣酱、麻油、椒盐等佐料。吃起来香辣可口。起初还有再尝的欲望,但顿一会儿后,便觉舌头被辣椒麻的难受,好象火焰山跑到了自己嘴里。赶忙灌上一大勺香嫩的牛腩汤,终于渐渐解除苦痛。爽,呵呵!
漫步在霓虹闪烁喧嚣嘈杂的大街上,身旁是陌生拥挤的人群,觉得自己是很难与这个沿海城市真正融合的。固然它的清静也会让我自失,但曾经淳朴的古代文明已一去不复返。
繁华的心境不属于我。走吧。
走过泉州
早晨醒来,不过八点半。
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书,有点烦。拨号上网,给朋友发了几封无关痛痒的E-mail,又懒怠与人聊天,那些话现在似乎显得干燥乏味,此时勾不起我丝毫兴趣。突然决定出去走走。先去泉州,再到湄洲岛。
给车站售票处打了预购电话,匆匆洗漱完毕,准备了简单的行囊,时间还充裕,便悠哉悠哉地漫步到车站。
这是个突然的决定。
路上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我已有些麻木。终于驶入市区,十多年前的记忆重温,熟悉而陌生。残缺的片段断断续续掠过,除了东西两塔的影子趋近于清晰,基本上淡却了当年的味道。
泉州话与chielle所在城市的方言虽然有些许不同,似乎鼻音重了些,但大体上还是一样的,毕竟同属于闽南语系,彼此的咬音腔调仔细点也能听得明白的。
泉州的街道很窄,巷子多,除非是新开发的城区,否则难得见一条四车道的路。交通秩序显得混乱不堪。行人、单车、人力车、机动车,你拥我挤,好象鬼子进村来了。步行街也远不如厦门利索,显得拖沓异常。可能跟交警的好脾气有关。
我一向不大会走路。走在大街上,常常自顾自地瞎想,不晓得观前顾后,平白无故的也会与人相撞。在这儿,更是晕头转向,左躲右闪,像只喝醉酒的鱼,迷顿在浑浊的海里。
在老城区,房子多是两三层的,很陈旧古老的那种。特别喜欢石雕的墙面,有些磨损,或者散布有裂痕,长着青苔,绿茸茸的。下面是枣红的砖墙,色泽在时间的流淌中退淡去,留下的是曾经的浮华、现今的感伤。木质的窗棱,已蜕变为灰褐色,那是历史记载下的沧桑。窗台上摆着一两盆瘦小的植物,黑色的背景撒上几点新绿,相互映衬,仿佛足不出户的小家碧玉。
店铺极多,可见当地人的生意经念得不错。但从他们的衣着看,品位并不怎样。总能看见一群一群服饰相似或相同的孩子。只会相互模仿,因此丧失了自我个性。
有些老字号,当年的石坊还在,但却已改头换面,做起别的买卖。物在人亡的意境尤为深长。也许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维持长久的。
去了趟古玩市场。
明知那儿的所谓古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假的,但想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又何必在乎真假呢。
器皿、配饰、字画、摆物等等,倒是没什么新奇能让我中意的,结果掏回一大摞连环画(小人书)。家中原本就收藏了不少,但有许多残缺不成套的,时常惋惜。这回便凭着印象将那些没有的买来,不亦乐乎。
一眼便喜欢上路边的刺桐树。这个时节花虽未争荣,但一朵朵的红微微点缀着高大的枝干,衬着这一年细密鲜绿的叶子,雕饰了古城泉州的凄艳。有点儿像木棉树,但花朵比它精致许多。
在开元寺内。
古木参天,清凉幽静,一派佛门净地。
大殿两侧的东西石塔可算是泉州的标志性建筑了。
“镇国”、“仁寿”两塔对望一千多年,彼此凭空敬畏,历经风雨侵袭、地震摇撼,仍威威仪仪显驰骋。
我把身子贴在锈迹累累的铁门上。除了塔外射入的淡微光线,几乎是漆黑的。只能隐约看见斑驳的石壁和小尊的佛像,有厚重的尘土气息和阴森的潮气。
铁门将内外隔绝,旁人无法窥探塔心的一切。禁锢的灵魂会游离躯体。
在古船陈列馆里,看到了1974年出土的泉州湾后渚海船。
曾经远洋的木帆船,在岁月的洗礼中被遗弃,湮埋于淤泥的污秽中。沉默,并不一定是对屈辱的低头,有时则是渴望重新闪耀的征兆。
清净寺是必去的。
对宗教有着特殊的喜好,自知尘缘缠身,难以了断,终归是个世俗的槛外人,但相信冥冥中生与灭的连横,神灵自明,必然度我。
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壹零零玖年),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座具有浓厚阿拉伯建筑风格的伊斯兰教寺。
它处在闹市中心涂门街中段,坐北朝南,门前的石板路看似新铺设的,喧嚣中保持独自的清宁。其中的许多楼宇已不复存在,所剩的主要有大门楼、奉天坛和明善堂。
大门楼用辉绿岩石砌筑,为圆形弯尖顶拱门。楼顶是平台,四面环筑“回”字形的垛子,单看上部,像长城的烽火台。但你绝不会将它与硝烟炮火联系在一起,它是平和的。站在下边,恍惚当心会突如其来地坍塌,将我湮埋在岁月流痕中。
原以为穆斯林习惯于露天的礼拜,这样显然更直接。后来才知道奉天坛的屋盖本是有的,在明朝年间倒塌,没有修复,就不再使用,祭奠搬到新建的明善堂。时光是肩负不起那样的重荷的。现在的坛看起来,相似于马雅文明遗址的某个建筑,一根根石柱林立,又像鲤城区浮桥笋浯村的生殖崇拜物----石笋。殿内四周的空地上花岗岩的残础隐约在草丛中,背负着辛酸与惨淡。
临近傍晚,搭乘公交车到清源山。
平日里是极怕长跑的,但却不排斥对爬山的喜爱。能够感受到犹如生命轮回的神妙。
不算崎岖的山路,已没有多少人迹,有时整段石阶上前后望不见半个影子。听到的,是林中诡秘的幽鸣。四围,满眼的翠绿炫耀着勃勃生机。沉浸其中,很容易抛开心中的阴霾,寂寞的难耐。
别人下山我上山。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偶然碰面,擦肩而过,互相投以一个友好、鼓励的微笑,或者一声亲切的招呼。同样是匆匆过客,他山他水巧相逢,算是缘份。但知道不可能再相见,无意间的邂逅只是留下模糊的面孔,很快就会忘却。
爬山确实很累。清幽的山林中隐约着初夏的燥热。纵然飘着微微细雨,但没走多大段,衣服已是湿透了。将裤脚卷到膝盖上,作用不大,反倒对腿有些压抑。只因是女孩,否则真想打赤膊,管他形象损了多少。
其实山中的景致与别处相比,并无什么较为独特之处。一样的山石,一样的树木,一样的亭阁,但去得并不后悔。因为始终偏爱山中的清泉。小股的水瀑缓缓地从石缝间泻下,极清澈明亮,像轻柔的透明丝缎,抚摩着山的肌肤,又像山的眼睛,赋予其干净的灵气。平静的心能够感受到它平静的流淌。
爬了一个多小时的山,忽上忽下,多是有石板铺设的。沿着标志指示,路过一个个景点,并不想作太久的停留。一再地重复相似的东西,会渐渐失去慧根,想保存印象中的灵秀。
在山上绕了好大一圈,终究是在累得迷糊中回到了山下。仿佛无尽生命的突然夭折,有的,或许是惆怅不甘的遗憾,或许是倦怠解脱的喜悦。
最后去的是老君岩。
平地上,硕大一块石像,七分天然三分人工。憨态可掬,掩隐在绿树青草中。风雨的雕蚀与洗礼,使它具有一股超脱的生气。
晚上,在铜佛寺的环湖小吃摊品尝当地的风味。
有那种一个一个的鱼丸、切成小块的土豆或芋头、长溜溜的豆皮串成的串,还有蔬菜的。用沸水烫熟了,再拌上辣酱、麻油、椒盐等佐料。吃起来香辣可口。起初还有再尝的欲望,但顿一会儿后,便觉舌头被辣椒麻的难受,好象火焰山跑到了自己嘴里。赶忙灌上一大勺香嫩的牛腩汤,终于渐渐解除苦痛。爽,呵呵!
漫步在霓虹闪烁喧嚣嘈杂的大街上,身旁是陌生拥挤的人群,觉得自己是很难与这个沿海城市真正融合的。固然它的清静也会让我自失,但曾经淳朴的古代文明已一去不复返。
繁华的心境不属于我。走吧。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 沪ICP备11026210号-1
版权所有 ©深秋小屋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13154293@qq.com ladyscn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