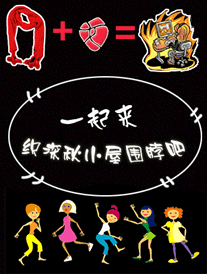【 2004-07-10 17:31:21 编辑:深秋小屋 字体: 大|中|小】
一.闺阁画――古代妇女绘画的基本样式
1.“技能”还是“艺术”――古代妇女绘画的非艺术本质
在中国,传说中的画祖是个叫“嫘”女性,于是,男人们无不遗憾地说:“可惜如此神奇的技能,是妇人创造的”⑴。这个传说的久远,使它在强大的父权制话语中,依然保留了明显的母性时代的痕迹,所以遗憾归遗憾,到底也还是认可的。而后世现实中的能画妇女却没有那么幸运,现在我们要在古代画史、画论中寻找女画家犹如大海捞针。幸而清代有个叫汤漱玉的女人做了这种“捞针”的工作,她从历代画史、画论以及其他史料的夹缝中,极力挖掘出200多个“能画的妇女”,辑录成一本《玉台画史》。事实上,这个数目只是实际能画妇女的一部分。因为,汤漱玉的辑录范围仅限于她所能见到的画史、画论和有个资料,而史料往往由于父权制的偏见拒绝记录女性的事迹,因此,未入史料的妇女肯定不在少数;该书的书评也说:“历代妇女能画的人较多,这本集子编录的并不能全部涵盖”⑵,可见古代能画的妇女并不少。
值得注意的是,《玉台画史》记录的这些能画妇女,不仅能画,还往往同时能诗善书、能歌善舞。如果我们把绘画以及诗歌、音乐、舞蹈作为“艺术”来谈论,这些技能都应该是最具形而上意味和最体现创造力的。然而,众所周知,中国的父权制话语对女性的严格限定,几乎将女性的创造力扼杀殆尽,那么,何以有这么多的女人又能够参与这种“创造性”的工作呢?我们不妨就以《玉台画史》所辑录的“能画妇女”作为分析文本,考察一下在父权制话语中,什么身份的妇女拥有绘画的“特权”,能画妇女以什么条件被记录,绘画以及诗歌、音乐、舞蹈对这些古代妇女究竟意味著什么。
①闺阁名媛和风尘名妓――拥有绘画“特权”的妇女
古代有可能拥有绘画特权的妇女只有两种人,即闺阁名媛和风尘名妓。《玉台画史》把能画妇女分为宫掖、名媛、姬侍、名妓四类,恐怕是出于作者对她们等级和身份的习惯性重视,虽然都是能画,但宫掖与姬侍怎能等同,名媛和名妓更不可同日而语,必不得已要一起谈论,只好按照身份严格分类。事实上,宫掖往往是入选宫中的名媛,而姬侍有许多都是从良的妓女。
能画的闺阁名媛,一般都出自家庭绘画世家,或祖父、父兄,或丈夫、亲戚都擅长绘画。这些大家闺秀虽然生活优裕、清闲,但家风严谨。深锁闺阁又身处绘画氛围,使她们不仅有充裕的时间而且有优越的条件接触绘画。因此,闺阁名媛绘画的可能性是最大的,《玉台画史》记录的这类能画妇女占一多半。其次的能画妇女就是名妓。与名媛相比,名妓的处境就没有那么顺理成章。如果不是能诗善画的风流文人成为她们重要的“服务对象”(嫖客),她们可能永远都没有靠近绘画的机会。一方面为了迎合服务对象的需要,她们必须学习,另一方面也使她们通过善画的文人服务对象接触到绘画。因此,古代只有这两种妇女有可能拥有绘画“特权”,而最终是否能够拥有这种特权,还取决于她们具体的个人才能,以及她们所处环境的宽泛程度等多种因素。
②才、色、贵、德――能画妇女被记录的条件
能画妇女,当然首先是能画。然而,能画的妇女很多,而历史留给女人的缝隙很小,所以,只是能画还不足以被记录。被记录的能画妇女的条件概括起来有几种情况。以“才”(有才气)被记录,才气往往是绘画技能高低的先决条件,这是自然;以“贵”(出身名门贵胄)被记录,在女性必须通过男性体现自我价值的社会,女人占她们父兄、丈夫的光,不足为奇;以“色”(生得美貌)被记录,在女人作为被看对象和欲望对象的父权时代,甚至也不难理解。然而,以“德”(具备贞、节、孝、柔等妇德)被记录,就显得很奇怪了,因为一个人的道德水准,与其是否能画、画得好坏,几乎没有必然联系,而在《玉台画史》中,这类被记录的能画妇女竟然占一定的比例。如“贾节妇有一幅画水仙的小画,纸墨还像新的一样。贾节妇是襄阳贾尚书的儿子贾瑾的媳妇,被元兵掠走,知道不能幸免侮辱,于是作了一首诗,投水而死”⑶;“汤氏,是计来的妻子。计来临死的时候,握著妻子的手说:我梦见你弹琴的时候琴弦断了,这是我死的征兆,请你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汤氏哭着说:如果我在,一定不会辜负你,但恐怕我也活不了多久了。计来死后三天,汤氏绝食嚎哭,第二天扶着棺材到墓地送葬,吐了数升血,竟然死了,年仅二十五岁”⑷;“贞女姜桂,年幼许配给某氏的儿子,还没有出嫁就守了寡,她父母想给她另外许配一家,姜桂哭着发誓不改配,于是不再强迫她。姜桂到老足不出户,缝纫之余,捎带着画画”⑸。这一类被记录妇女,几乎没有自己的姓名,被记录的事迹也主要是贞节孝柔,而能画只是随手带上,有的则索性不提。而且,有才、有色、出身贵族都无法自己决定,而唯有“德”可以自己选择,这种选择无异于甘心情愿把自己送上祭坛,也就格外重要。虽然都是“能画”,但被记录的标准不是绘画本身的品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绘画对于妇女,与同时的文人画家有本质的区别。
此外,能画妇女均是以男人的附属形式被记录,没有独立的身份。如某某女、某某妹、某某母、某某妇、某某配、某某妾、某某侍人、某氏、某夫人,甚至某某曾孙女、某某姑母、某某侄女种种。总而言之,她们必须通过一个与她们有关的男人来确定自己的身份。能够获得此“身份”者,不是闺阁名媛就是良家妇女,其他没有身份的则十有八九是风尘女子。因此,同是能画,名媛最怕的即是把她们与名妓混为一谈,从而有失身份,她们往往不肯把自己的诗画示人,甚至不惜毁掉,生怕流传到闺阁外面,被人误认为是名妓所为。由此可见,无论在男人眼中,还是女人自己的观念里,是否能画并不重要,能否画得好更不重要,而重要的只有名节和身份,而对这种名分的执著,几乎把女人从历史中抹掉了。 ?????
③琴、棋、书、画――闺阁名媛的家传修养,风尘名妓的生存资本
能够接触到绘画,并不等于可以把它作为艺术来对待。事实上,对于大多数能画的妇女,绘画只是一种技能,而且是为了某种具体的实用目的被训练的多种技能之一,所谓琴、棋、书、画,即是对她们多种技能训练的概括。由于身份和处境的不同,决定了她们学习这些技能出发点的不同,名媛们主要是作为一种家传修养,消闲自娱;而名妓们则作为一种生存的资本,应对娱人。琴棋书画的意义都是如此。既是技能,她们一般都是同时会几种,只是各有偏重。同时会写诗作画的最常见,也有一些兼而擅长琴棋音律的。值得注意的是,琴棋书画作为技能,在名媛,不仅与女红如刺绣并提,而且还往往作为女红之余的副业,如“蔡国的长公主,聪慧有悟性,六岁就能弄笔书画,也喜好绣花女红类的事物”⑹;“殳默,九岁能作诗,刺绣剪裁,没有不精妙的,还会写小楷、临摹画”⑺;“李夫人自叙说,我丈夫双井公,把兰花比作君子,父亲东野翁很喜爱兰花,我也很喜爱兰花,每每作女红的闲暇,试着画画兰花,自己为闺房的玩事增添些乐趣”⑻;“谢夫人早晨鸡一叫晨就起来,家务事做的没有不周到的,除此之外就读书看古文,再有时间就书法绘画,这两项都非常精通”⑼。在名妓,绘画往往与歌舞、色相等媚人术共语,如“严蕊,擅长琴棋书画、歌舞丝竹,相貌和才艺都是一时之冠,偶尔作诗词,也有很新奇的句子”⑽;“卞敏,身材修长苗条,皮肤洁白如凝肪,风情优雅,也擅长画兰花”⑾;名妓薛素素的记录更说明问题:“薛素素,能弹琴调筝、织布刺绣,也擅长化妆打扮,人世间可喜可乐愉悦男人的事,种种都出自她的手。但是青春过后,人情不免想有家庭有孩子,薛素素在这方面使不上劲儿,所以现在她以精湛的绘法画一些观音大士,为天下有情夫妇祈求子嗣,对于她自己,也弥补了一段大缺陷”⑿。由此可见,对于大多数能画妇女,绘画并不意味着形而上的“创造”,而只是一种形而下的技能训练之一。名媛们作为修养消闲自娱、为父兄们争脸面也罢,名妓们作为资本献媚娱人、博男人们的欢心也罢,都是向与她们有关的男性讨喜,就这点而言,绘画对她们并无本质的区别。我们统称她们“能画妇女”要比为“妇女画家”更确切。
即使如此,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悬尺下,如同她们要掩饰喜怒哀乐的幅度,她们还必须控制才智的施展尺度。如“马娴卿,擅长山水白描,画完就用手撕掉,不拿给人看,说:这怎么是女人做的事呢”⒀;“傅道坤,相貌美丽而且聪慧,从小学习画画。被范生娶回家一二年,从来没有显露过会画画。后来有一个元宵节在街上张灯,灯带偶然忘了画,众人急忙找绘画的高手,傅道听说了,提笔就画好了灯带,观看的人竞相赞赏”⒁。绘画对于这些古代妇女,本来已限定颇多,又如此躲躲闪闪,再加之整个父权制话语对女性的习惯性压抑、歧视和忽略,画艺精良都很难,更不用谈有创作色彩的艺术作品。因此,这些能画妇女虽然不少,但稍能突破限定,可以象男性文人那样以绘画写意抒情的妇女画家就微乎其微了,她们必须同时拥有某方面优越的环境和出色的个人才华,她们是能画妇女的特例。
2.女性内心感觉的书写――“闺阁画”的艺术评判
尽管绘画对于能画妇女是作为技能训练学习的,但她们接触的“文人画”毕竟是中国艺术传统的最高体现,而且有特别和完整的评判标准。当然,这个标准不是女性的,但如果我们要妇女绘画的“艺术”价值,这是唯一的标准。追求笔墨情趣的表现,奉淡泊、出世为最高境界,标志着中国古代占主流地位的士大夫艺术传统的基本特质。宋以后的文人画,确实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宋以后知识分子普遍的避世、淡泊的心态。这种避世心态,原自于他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信条,而文人画即是他们不能兼济天下只能独善其身,即他们在现实中政治理想丧失后,退而寄情山水的产物。尽管,文人画的追求淡泊,放弃了对现实的关注,但这种精神现象的产生却直接导源于现实。当然,也正是由于放弃了对现实的关注,文人画最终成了士大夫手中的把玩式的闲暇逸事。而文人画追求的淡泊逸气,以及笔墨表现,无疑是艺术达到最高层次的标志,而且正是淡泊逸气这种形而上的内涵,使文人直走到笔墨与心灵直接对应的层面。简单地说,笔墨传达心意的优劣即是古代文人画的基本评判标准。
然而,古代妇女无论名媛还是名妓,几乎没有机会与外面的社会接触,“闺阁”就是她们终生的生活环境,她们再有想象力也很难获得超出闺阁的感受,能画妇女也不例外,她们的作品也因此被称为“闺阁画”。从流传下来的妇女绘画看,花鸟画大都是花花草草、鸟鸟虫虫(附图1-2),人物画大都是闺阁生活(附图3)和少量的观音大士,最能体现文人画“退而寄情山水”、笔墨与心灵直接对应的山水画,极少出自妇女画家之手。即使花鸟和人物,能以其特别的处境和超凡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局限,以笔意写胸意的妇女画家也是凤毛麟角。如管道升的《墨竹》(附图4),用笔劲力而洒脱,墨色苍莽而清爽,几乎不是画而是书写出一种豪放不羁的气度和一丝心高气傲的孤独和苍凉,如她自己在一幅墨竹上的提诗:“竹势撒崩云触石,应是潇湘夜雨时”⒂,这大概是古代妇女绘画的最高成就了。薛素素的《兰草》(附图5),“下笔迅扫” ⒃,灵气中微露伤意;马守真的《兰石》(附图6)构图很特别,或“在起伏不平的坡地上,丛兰与竹石相伴而生,纵横错落,生机无限” ⒄,或怪石居中,以重墨渲染,而兰草于石后,以淡墨书写,墨色润泽,很有些处逆境而自洒脱的意韵,这恐怕也是马守真“幽兰生空谷,无人自含芳” ⒅的自喻和“喜轻侠”的性情写照。她们与文人画借松竹兰梅等花草抒怀的模式一样,也多以兰草梅竹为寄情对象。然而,与士大夫的对淡泊意境的追求不同,她们书写的情怀、感慨和性格,多是源自女性内心的,而与现实尤其社会政治没有太直接的关联。
我们在古代画史、画论的夹缝中,可以看到对这些出色的女性画家及其作品的品评。中国古代画论很重视画品的评判,即绘画通过写意抒情所达到的某种境界,而境界的评判标准是一个感觉的标准,所以称为意境。意境因画家的个人气质、人品、修养、才能的不同,不仅有差异而且有高下。对妇女绘画的评判虽然也是这种品评的方式,但我们从中只能看到其“品”的共同性,而感受不到品的个人化特质。这种共同性有两种不同的倾向:其一,体现“女子本色”,即体现女人本来特质,如“看这幅画的用笔意味和题词都很清丽委婉,好像是女子所为” ⒆;“感觉清淑的气韵,果真钟情于女子”⒇,总而言之是“温柔妩媚而有韵味,清纯美丽而有情致”(21),这与父权制话语“女人味”的标准同出一辙。其二,“无儿女子态”,既脱离了“女人味”而具有男子气概,如管道升“用笔熟练洒脱,纵横苍劲秀丽,绝不是一般女人的状态”(22),“笔墨具有远古的气韵,没有小女子样子……这卷竹枝画,纵横笔墨美妙,像是披风带雨,又好似公孙大娘舞剑,不是闺秀本色一类”(23);仇珠“一扫脂粉女子的样子,真是女人中的伯时(伯时,宋名画家李公麟)”(24);范珏“笔墨间具有天然的气韵,是女人中的范华原(范华原,宋名画家范宽)”(25);寇湄“点缀了竹石的情调,洗却了女子的姿态”(26)。很明显,以衡量男人的标准做评价和比喻,是评判出色的妇女画家作品的常用语,也是妇女画家在父权制话语下获得的最高待遇了。这两种倾向导致了两种评判标准评判的结果,简而言之,一种是象男人眼中的女子的,一种是直接象男人的,然而,这两种评判标准无疑都没有逃离男性的价值尺度。对于从创作到评判都根本没有自己的尺度的能画妇女,以“女子本色”为基本准绳,以“无儿女子态”为最高原则是一种基本现实,而且已经是她们在绘画乃至生活中超越女性规范的最大限度了。这些妇女画家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达到或者接近了这种标准,得以入列文人画家的队伍,而大多数流传下来的妇女画家的作品,无论从题材、风格、手法和语言方式上,都没有超越文人画的男性审美尺度,也没有达到文人画的最高成就。
二 .“新闺阁画”――当今妇女绘画的主流样式
1.还原的“女人味”――当今妇女绘画女性价值的重新陷落
由于全权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功利主义对人性压抑,也埋下了它否定自身的种子。19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新时期首先出现的社会背景即是“人性复归”。人们尤其是文化人最渴望的是摆脱长期以来政治对人性的控制,甚至希望借西方的民主来拯救中国拯救自己,但这些社会思潮的倡导和参与者大多数是男性。而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绝对平等的“无性别”原则规范下,以牺牲自己女性本身为代价,吃力地顶着“半边天”的妇女,大多数则走了一条完全逆反的路。她们不用任何的宣传和运动,也没有任何的口号和说法,就本能地渴望把自己还原成为“女人”,因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解除把她们压迫得变形乃至变性的重担,自然地喘一口气。然而,除了传统的女人模式,她们依然是没有别的标准可依。对社会给与的“半边天”角色的复杂的恐惧心理,使她们更加渴望回家寻求庇护,所以这一“还原”,她们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接受了传统女人的基本生活观念:居家、闲散、与世无争。
这种境况自然也反映在女性绘画上。作为对毛模式革命现实主义阻隔艺术自身规律的发展,排斥中国艺术其他样式产生的可能性的逆反,1979年以后的十几年里,中国几乎把中西方古代艺术传统、西方现代艺术传统的各种流派和样式都翻用和尝试了一遍。女画家虽然也跟随着公共趋势,尝试了革命写实主义之外的各种艺术手法,然而,摆脱了革命现实主义男性标准的同化,她们依然找不到可以泊靠的女性堤岸,对革命功利主义的避之如虎,使她们连社会题材都害怕触及,更加无家可归的状态,使她们“回归女性自身”的原初愿望,在观念上自觉不自觉地落脚在了传统艺术的家园。
这个时期的女画家人数多、作品多,但其一,艺术观念与古代妇女绘画并无多大差异,绝大多数题材集中在女人、儿童、母子、花草、风景上,几乎是“闺阁画”的现代翻版。看不到女性意识的突破和对当代女性生存状况、当下女性问题的追问、个体生命感觉的反映,总而言之,与中国当代文化尤其女性文化无关;其二,语言模式尽管使用的手法看上去“多种多样”,但既没有逃离各种公共化的传统语言模式的藩篱,也很少同期男性艺术家对西方现代主义手段的模仿性尝试,以至于整个1980年代中国轰轰烈烈的现代艺术思潮中,几乎见不到女性的身影;其三,评判标准依然是男性化的或者说是公共化的,除了与评论男画家绘画一样的表面化地讲述生平经历,描述画面手法,妇女绘画常见的评语依然是清新娟秀、简洁稚趣、天真自然、童心稚气、轻柔秀丽、清纯温馨,纯情,轻松、明快、稳重清丽、明快端丽、温柔典雅、大胆泼辣,大体是闺阁画评语的根基加女英雄性格的点染,无非是“有女人味”和“象男人”,这两种标准我们并不陌生,它即是古代妇女绘画男性化标准“女子本色”和“无儿女子态”在现代的延伸。我姑且称其为“新闺阁画”。
2.嫁接的少女梦――“新闺阁画”畸形的社会根源和延伸的影响
这种“新闺阁画”样式,1980年代初开始形成,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也是中国的现、当代艺术崛起的时代,不仅没有发生根本的观念性改变,反而作为一种妇女艺术的“主流”模式固定下来。“新闺阁画”有着千篇一律的共同特点:题材上强调画生活――花花草草、纯情少女、温馨母子;观念上视纯情纯真为最高的审美境界――阳光灿烂、优越闲散、美梦甜腻;画法上追求学术性――把公共认可的中西艺术的某种技法作为模式固定下来,强调技术性――刻意追求技巧和制作上的精细,就怕人家说她们不是“女人”画家。这类作品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妇女艺术数量最多的作品,因其与目前官方艺术院校倡导的“主流”艺术一母同胎而最被官方和公众认可和接纳(附图7-12)。但遗憾的是,这种作为“主流”的妇女艺术样式,犹如庞大的官方意识形态上柔化的装饰品,几乎与中国的当代的女性意识和生存状况无关。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由于涉及到历史、社会政治、乃至女性心理显得有些复杂。“新闺阁画”的奠基人是1949年以后所谓“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女画家。她们出生于1930-40年代,旧式的闺阁生活在她们童年中留下了梦幻般的影子;1950-60年代中期,作为“新中国”艺术院校培养的第一代女艺术家,她们接受了全面的革命人生观的改造和革命写实主义艺术观的教育;1960-70年代,一场文化革命席卷了她们一生最美好的青春热情和创作年华;1980年代初,当她们五六十岁由中年步入老年到时候,却“痛苦地发现其一安身立命的艺术大厦正在倾倒”(27)。短短的半辈子,她们几经社会价值观念的重大失落。社会补偿给她们在艺术界最高的地位――艺术院校的教授、著名艺术家,但这弥补不了失去的青春年华及其梦想,弥补不了心灵造成的巨大伤害和反差,作为艺术家的观念转变更是难上加难。这种困境是整个这一代画家乃至整个社会的,不只是女画家。1980年代初,这一代画家举办过一个“半截子画展”,曾经轰动一时。半截子画展前言:“先生说我们是没出壳的鸡,后生说我们是腌过的蛋……”(28),道出了他们发自内心的尴尬和悲哀。大起大落的社会现实,不仅吞噬了他们的青春和热情,桎梏了他们作为个体人的思考方式,也粉碎了他们内心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人过中年,一切都不可能重新开始,他们只有拾起碎片,并鼓起最后的勇气和精神,运用一生的才智和技能拼凑这些碎片。
这就构成了这一代的女画家心灵的两个巨大的落差。其一,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张扬了她们的青春热情,但却压抑了她们作为少女的美丽、温情,人生的必经的梦想时期,被尘封得不见天日。等社会环境容许开启这些梦想的封条的时候,她们青春已过,少女梦想早已如风干的花朵,而对少女梦想的渴望,却因其无法寻觅加倍涌来,成为她们创作乃至生活的不可抑制的重要元素。其二,传统的女性教育,使她们对大家闺秀、贤妻良母的中国传统女性模式情有独钟。而革命时期的政治要求,使她们身体走出了小家庭,抽离了古代闺阁生活严格的限定造成的禁锢和寂寞,但却从精神上压抑了她们对“闺阁”象征的养尊处优、居家闲散的生活方式的千丝万缕的眷恋。如今,政治要求虽然撤离,但心灵上留下的阴影,却使她们很难毫无羞涩地面对这种真实而抽象的心理状态。因此,眷恋只能作为一种无法落脚于现实的精神性假想,也成为她们创作乃至生活的不可抑制的重要元素。
对我们妈妈这一代在“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度过青春的女性,在艺术界,即作为“新闺阁画”的奠基人和最重要代表的女画家,我们应怀有很深的理解和同情。然而现实总是残酷的。这一代的画家,在1980年代以后,大都享有高等艺术院校的教授、著名的画家的地位,也就是说他们掌握着教育和引导下一代乃至几代艺术家的特权。因此,这一代女画家由于特殊历史原因造成的“新闺阁画”的观念,如同畸形的遗传基因,一直延伸给了下一代乃至几代女艺术家。如今,中国女艺术家虽然表面呈现几代同堂的格局――这一代从革命现实主义过渡出来的(60-70岁),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的画宣传画、连环画起家的(50-60岁),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大批年轻的(30-40岁),甚至1990年代所谓“新新人类”的年轻女艺术家(30岁以下),大多数至今依然在这种观念下创作和生活。官方的全方位认可,更无疑使这种“新闺阁画”作为中国妇女艺术的“主流”样式地位稳固。这真是一个天大的遗憾。
注:
⑴张萱疑耀》引许氏《说文》
⑵沈颢《画尘》
⑶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
⑷吴其贞书画记》
⑸郭锈《吴江县志》
⑹《书徵续录》
⑺《范太史集》
⑻《榫李诗系》
⑼王恽《秋间集》
⑽郑侠《西塘集》
⑾《齐东野语》
⑿、(25)、(26)余怀《板桥杂记》
⒀《明诗综》
⒁《金陵琐事》
⒂ 管道升题画诗
⒃《静志居诗话》
⒄李匙《明代名媛名妓绘画艺术比较》,《美术史论》1992年第一期。
⒅马守贞题画诗
⒆杜琼《东原集》
⒇、(21)《珊瑚网》
(22)《图绘宝鉴》
(23)卞永玉《式古堂书画汇考》
(24)钱大昕《跋》
(27)陶咏白《女儿国的圣歌》,《中国当代女画家-序言》,1995年。
(28)《半截子画展-前言》,1980年,北京。
廖雯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 沪ICP备11026210号-1
版权所有 ©深秋小屋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13154293@qq.com ladyscn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