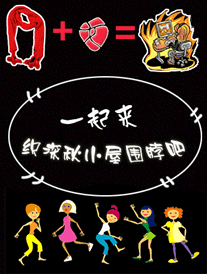【 2005-12-26 19:01:53 编辑:深秋小屋 字体: 大|中|小】
――玛格丽特杜拉斯
在印象中的张爱玲永远是一个凄婉的“怨妇”形象。一方面,她的古典式的哀愁是在吟风弄月中提炼出来的;另一方面,也来源于她的生事与在繁华都市中的生存经验。值得指出的是,她并不是祥林嫂那样的怨妇,她之所以美,正因为他的哀怨中隐含了一种莫可名状的暴力。当然,适当的暴力并无可厚非,尤其是如张爱玲一般,带有撒娇意味的暴力与其说是暴力,不如说是一种倔强的反抗。这正是她作品中的可爱之处。

就比如《倾城之恋》中,她不惜用陪葬香港一座城市为代价,来换取白洛苏与范柳原的爱情。一次小小的“暴力”(当然,作者拥有上帝般的造物主能力,这也不能称其为完全的暴力手段),促成了一对旷世绝恋的感情。或许也只有在张爱玲的心中才会把如此轰轰烈烈的经历打造成凄美的爱情。白洛苏丧偶之后,仍然居住在男家,“善于低头”成了她最赋有东方女性美感的习惯。情感与地位上的双重压抑,为她日后的倔强与反抗埋下了种子。一个是东方的爱情观:爱情即婚姻;另一个是西方的爱情观:爱情非婚姻。非要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这样的差异才能够得以调和。在一个被设置在各种暴力冲突中的爱情,突然走到了一起,这无疑是张氏小说的惯用手法。白洛苏的爱情观里,爱情即是走向婚姻,或多或少都残留些旧式女性的功利心理。范柳原深受西方文化的感染,那种带有骑士精神的浪漫背后常常也伴随着玩世不恭的特有的情调。于是,他们两人开始了一段漫长的高级调情:彼此相爱,却又若即若离;互相追逐,却又互相逃避。突然,暴力来了,家庭地位上的压抑使得她跟随他远走香港,香港的炮火里又熏染了他们的爱情。就是这样,不可靠的年代里,毫无安全感的环境里,什么都有可能成全,什么也都有可能毁灭。对于痴迷于真实情感至上的张爱玲来说,她的倔强不惜毁灭一座城市,也要成全一场真爱的延续。当然,这与她自身的情感价值趋向是分不开的。
在她其他的作品中也无不表现出这一点。《半生缘》里顾曼桢是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新女性,叛逆、坚强、刚毅又不失温存的性格在她的身上得到融合。若不是,出于对孩子的考虑,她的倔强将不可能磨灭。毕竟,有时候亲情的因素是可以毫无理性地磨灭一切其他性格的。又譬如,《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情欲压抑的缝隙中最终爆发了。她的变态可以看作是倔强的无限升华,情欲扭曲下的她可以不顾一切伦理道德,可以不顾一切儿女亲情。她的暴力既摧毁了别人的幸福,也摧毁了自己。
当然,说张爱玲的小说中具有暴力因素,只是就五四新女性的觉醒与反抗而言的。然而,正如那个时代所有的局限性一样。在传统礼教中浸染了近一千年的女性在无意识中又是难以彻底反抗的。就如白洛苏虽然想反抗,但她仍旧把爱情当作婚姻的功利性过度。顾曼桢也因万般无奈而在她姐夫的淫威下最终妥协。种种的悲剧结局不得不说张氏的小说是悲剧性收场的。正是在这样的强烈的悲剧感与淡然的反抗中,她的小说主人公的美感才体现得淋漓尽致。女性特有的哀婉的暴力,在各种矛盾冲突中引发。就如杜拉斯说的――使我感动的是我自己,使我想哭的是我的暴力,是我。一对矛盾体,同时惹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既有东方古典的一面,又有西方的因素。有时候,美感往往就是在矛盾的合理碰撞中擦出火花的。
这不仅是她小说主人公的性格,也是她这一时代的女性共有的精神特征。张爱玲生活在父母情感破裂的生活中,承受父亲暴戾的漫骂与责备,甚至是关禁闭与受毒打的惨境。对于父亲的冷漠与反抗,成为了她成长过程中的人格缺陷。对于母亲的渴望又使她在性格的另一个维度同样遭受缺损的不良反应。按照弗洛伊德的分析,每一个女孩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的伴随着“恋父情结”――即倾向于父亲而背离母亲。然而,张爱玲似乎是个特例。她仇父的性格与对母亲空洞的想象已经将“恋父情结”彻底地洗涤干净。这正是她性格缺陷的根源。换言之,张爱玲的叛逆心理与反抗精神就是源于“恋父情结”的丧失。
这直接影响到她自己的恋爱经历。年纪大她许多的胡兰成终于出现在她的生命中了。就如他在《今生今世》里对自我的描述,他是一个旧式才子,既有对在特定时期对某一个人钟情的一面,又有在不同时期对多人有难以言说的特殊感情。张爱铃爱上了一个暂时专一的情场老手。一方面是当时如同张爱玲一样写作风格的鸳鸯蝴蝶派不受主流文学的认可,而胡兰成却对她有异常深刻的赞誉,另一方面是由于胡兰成的细心关注与老成持重的性格更适合于张爱玲。于是,他们的爱情就开始了,在一种叛逆心理的怂恿下悄悄展开。当然,很难确定,他们的老夫少妻关系是出于绝对的爱情。很有可能,胡兰成的出现只是填补了她成长记忆中对于“恋父情结”的缺失。在古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的“恋母情结”也是以悲剧告终。而在张爱玲的生活中也同样没有能逃脱这一经久不衰的母题。对于她而言,反抗精神促使她冲破原本的家庭与世俗礼教共同编制的藩篱,而冲破了一层之后,她却突然发觉自己闯入了另一个牢笼。就像钱钟书《围城》里讲的一样――城里的人想冲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然而,这并不是悲剧的本质。根源所在是当你凭借着莫大的勇气和反抗的实际行动冲破了一个牢笼时,你却不经意地发觉,你已经站在之外的更大的一个牢笼中。
同样是悲剧的结局,同样是哀婉的暴力。发生在她笔下的人物中好歹成全了爱情,而在她的人生中则是一个过场般的悲剧。当然,从审美的角度来说,两者都具有相当的美感。然而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她的作品作为对她自己自怜自爱的一种补偿,却是对她本人最大的“求之而不得”的怨妇心理的写照。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 沪ICP备11026210号-1
版权所有 ©深秋小屋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13154293@qq.com ladyscn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