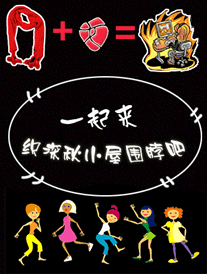【 2005-10-03 11:26:59 编辑:劳拉 字体: 大|中|小】
天堂归来话女性―记三个离了婚的中年知识妇女
好久没去杭州了。杭州真是个天堂,它是爱情的摇篮,旅游的圣地,会议的天堂。西子湖畔,人群熙攘,比肩接踵。‘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就连九百年前的封建老先生也明白,西湖和西子般的女人,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年青的,打扮得那么素净,象东山魁夷的画子;中年的,却打扮得那么妖艳,如倒翻了的彩色盘子。无论是“袖珍型”的、还是“豪华型”的,女人们都在西子湖边展现着她们的风采。
在杭州,我有缘接触了三位女性,三个离了婚的中年妇女。
A
她长着一双丹凤眼,眼睛里镶嵌着两只开始混浊的眼珠,眼角的鱼尾纹却盖不住她青春时的美丽。在办公室里,看到我的突然出现,她一反平时轻声慢语的习惯,居然高兴得叫出声来。
我:……您好吗?
她:我?……很好!手续办了两年多了。
我:……现在感觉怎么样?
她:现在?……我只有一种感觉――解脱了!
我:解脱?
她:是的,解脱!我好像是从绳索的捆绑中解脱出来了,手脚都能自由的活动了。
……离婚……真不容易啊,在中国离婚要比结婚难,当然,双方协议离婚的除外。
想起当初结婚的时候,赞美声一片,仿佛男人和女人的结合是条件的互换,只要将经济、外貌、家庭出身、文化水平、身材高矮这些条件放在天平上一称,在世俗的观点看来条件相等了,婚姻也就美满了,就像婚姻介绍所的布告栏上贴的那样。
如果说条件,我们俩是够般配的了……可婚姻真的不是方程式能算出来的啊。
我:你们俩的分歧是……
她:因为婚姻不是买卖、不是物质的交换、不是1+1等于2的数学题……
我们结婚得很晚,双方性格都已定型,没有年青人那种盲目和冲动。结婚后我慢慢的发现,双方都想改造对方,这是不可能的了。我越来越感到,他只是将我当成他的附属品,我只应该为他而生存。他的事业才是我们家的事业,他的前途才是我们家的前途。我的一切作为只应该是他前进道路上的润滑剂。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是个贤妻良母。可悲的不光是他这么认为,他的父母、兄妹、朋友、同事,甚至包括我周围的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开始怀疑“我”是否还存在了?我是否只配当他的影子?
当我尝试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或对他的事提出些建议时,他就大为不满,指责我不尊重他。我就奇怪了,就问他,难道他不知道这是他对我的不尊重我吗?他便光火了!(当然,还是温尔文雅的姿态,他从来就是很文明的。)危机就是这么开始的。
我:能不能说你们的离婚是由于爱情和事业上的矛盾?
她:不!不是的。我不是那种事业性很强的女人,我只是想完成我的本份工作,人应该对自己负责。
我的生命几十年都在磁带的运转中消失了,但是我乐意。那些长篇小说的选播、电影录音剪辑、广播剧的制作、文学评论……听的人从来没想到过,有这么个老女人,这么个电台的文艺编辑,每天坐在录音机前,要让磁带转上几千圈,甚至更多,她才能审定节目,算出时间,写出目录,决定发稿。(这里还没将创作和制作节目的时间算上。)在这个位置是出不了名的。我愿意做机器的一部分,我并不追求那种光辉灿烂的事业,怎么能说我们是爱情与事业的矛盾呢?
我:离婚后你难道没有一点失落感?
她:失落感?你指的是寂寞吧。我每天清晨六点半打开收音机,录下英语函授课文,七点骑车去上班,吃食堂,转磁带,晚上七点回家,急忙学早上录下的课程,还要抽时间看书,看电视,一天下来又忙又累,我很充实,没时间去寂寞。不过……有时也会有的……在熄灯的刹那,当黑暗象锅盖那样罩住我的时候,我会有点茫然,就会想起那不在我身边的小女儿。
人不能没有希望,我还有三年就退休了,我的希望就是她。我相信她不会象我们这代妇女这样,生长在新社会却被老的道德羁缚,她一定会有新的环境,新的自我。
我:哪……你现在发现自我了?
她:(笑了)……不知道……如果当时牺牲我的“自我”,成为他的附属品,或以他为我的归宿,也许我俩就没有矛盾了。你别笑,中国女人几千年来没有过“自我”,现在开始有了,太不容易了,太可贵了!中国老妇女的“自我”终将苏醒。我想,只要中国的男人们承认老女人们也该有“自我”,那么也许离婚率就会降低,特别是在知识界。
我:(愕然)……
B
这是一个我不认识却又比较熟悉的女演员。她的知名度不算低。正当她在艺术上臻于成熟时,她调离了培育她的第二故乡。
她离了婚。
是不是因为离婚了,只好改换个客观环境,才能从容的生活下去?也许...? 她像个"谜"一直吸引着我。我想采访她,但是不敢。婚姻家庭这类题材对有些人来说是属于隐私范畴。
一天,我被人拉到某所高等学院去帮忙排戏。临去我带上这个谜,终于设法接近了她。
她那双眼睛象两潭深水,长长的睫毛忽开忽合,显得很端庄,矜持。她处于对来自第二故乡客人的礼貌,对我的来访淡淡地应付着,偶尔地对答几句,气氛简直象那间没有窗户的客厅。
此后我总是找一切机会尝试着去接近她,但她却像一尊包裹在透明薄纱中的忧郁的雕像,可望而不可及。我和她谈她生活过多少年的第二故乡,告诉她,她的老团长还希望她回去;和她谈到过去岁月中她所熟悉的人和事,试图唤起她对过去的回忆。她在话题的外围周旋着,一遇核心问题,便小心翼翼的回避了。一种淡淡的哀愁笼罩着她,她不愿回顾往事。在忙碌时她是敏捷的;在闲暇时她是宁静的。我感到她有一种隐痛在身,而我却无法帮助她,不能帮她摆脱那张没人看见也没人肯承认的网。
她的心总萦绕牵挂在女儿身上,一米六几的女儿,寡言、秀丽,很像她。有天排戏晚了,大家都劝她把女儿接来一起用餐。她写了张便条当介绍信,不然女儿是不肯跟陌生人走的。车去了很晚才回来,去接的人说,打门许久,没人开门,原来女儿在沙发上睡着了。女儿却说,妈说过的,不管什么人打门,别理睬.....这么大个女儿,还像个娃娃,大家笑了,我可笑得有点苦涩。没有男人的家庭往往会这样。
一个很不错的演员,为了躲避一种什么力量,单身带着个孩子想方设法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躲避流言,消除猜测,艰难地生活着。
几十年的舞台生涯,她曾塑造过多少令人难忘的角色。俏丽的少女,端庄的知识分子,雍容华贵的妇女.....同样,在人生的舞台上,她也希望扮演一个理想的角色,但这却不容易做到。过去她有过多少少女的梦幻,而今她不会再有了。人生的周期不可逆转!
每当我想起她那双略带戒备、略带忧愁的眼睛,总感到她的生活并不完美;已经消失了的"昨天",常常给她的是带有阴影的"今天"。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都只认为核心家庭才是真正完美的。对于那些单身的、离异的家庭总爱议论不休,指责个没完。这种无形的压力,对一个坚强的女性,还可小小抵抗一阵;而对柔弱的女性来说,无疑是一把无形的利刃,是一种残酷的压力。
我无权对任何人的婚姻选择做出评价,但我这次采访,让我看到了她,看到了她的周围,尤其是感受了她那种换了环境还依然存在的压力和那张无形的网。
我在想,如果有一天,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一个离了婚的女人能不被社会议论,在她的周围没有那张无形的网和无形的压力,而有一种正常的环境气氛,这对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来说,是多么的可贵和重要啊!
C
她刚拍完一部电视剧,初剪结束了,趁这空隙,我俩见了面。
乍见到她的人,都认为她颇有男子气概、大将风度,高高的身材,开阔的五官,说起话来声调不高,却果断有力。
我知道她很忙,打算寒喧几句便走,没想到一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了场。她谈到她的创作计划,拍片的艰难,女导演的苦衷,资金短缺所造成艺术上的遗憾……她说这些就象一行没有标点符号的长句。
她的家坐落在市中心,熬过多少岁月才有了这套不太完整的一条龙式的住宅。室内清洁整齐,无论地板的颜色、墙上的布置,看得出这是女主人格调之高雅。也难怪了,她年青时是学美术的。
又是一个离异了的女人。
一只青蟹,一盘冬笋炒青交,一锅肉汤……正准开饭,儿子突然回来了。真怪,她的脸上顿时增加了许多柔和色,母性一下子就从她所有的毛孔里洋溢了出来,我惊喜地看到了第二个她。
儿子俊俏、高大、削瘦、腼腆,一头钻进了自己的卧室,关起门又摆弄他的摄影,连喊几声叫他吃饭还不肯出来。
席间,我无意中谈起了别人的爸爸,她立即用眼光制止了我。
饭后儿子走了,她轻轻的叹了口气说,二十几年了,他从小就“没”了父亲,一听到别人说这个词,他就特别敏感。怎么办呢?能给他的我都给了,唯有他的亲爸爸,我却无法给他……
从几千里之外的北方调回杭州,带着他生活了这些年,容易吗?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常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和困难。
离婚,这个字眼对目前有些青年说起来就象吃豆子那么容易,其实,在五十年代,一个女人、一个生活在这块封建意识特强的国土上的女性,要走到这一步,不是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的啊。且不谈生活上的困难,就是社会上的流言,背后的议论,无形的压力会使你比正常人的生活困难得多。仿佛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只是件残缺不全的工艺品。
女人不好当,有头脑的女人就更不好当,想干点事业的女人就会更更不好当了。社会现状放这儿了,旧的道德观点放这儿了,有时不只是别人的指责,连自己都会指责自己:不像个女人。许多人爱唱“女人不是月亮,不靠男人也能发光”。其实一个女人太“亮”了,有几个男人能忍受的?
有些女同志信任我、找到我,将自己家的矛盾、个人的隐私对我和盘托出,希望我能用我的爱情经验给她们作前进的坐标,为她们寻找到一个平和的港湾。我真的为难极了。要知道,家庭是千姿百态的,我的经验对别人是毫无用处的。现在有些法院判起离婚来,恨不得将条文放到计算机里去找答案,其实人的情感纠葛是无法用理智去计算的。
不管怎样,我也算是个过来人了。要我说说离婚几十年的感想……现在我会对有矛盾的中年妇女说,还是少离婚的为好,世界上多几个“家庭维持会”,对社会、对个人是没什么害处的。这也是不是办法的办法,年青时男怕女飞,中年后女怕男飞,没办法,人的生理现象决定的。有些人老是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一个女人老了,有些男人就不爱了,找个借口说是感情不和了,个性不合了,吵着要离婚,女人随便的离了了,离了又对谁有利呢?
“果实吹嘘自己的财富,它们故意不提花儿的贡献。美丽的花儿,从花蕾到开出鲜艳的花朵,最后还将自己的身体掩埋进泥土里,化做养料去滋养那果实的成长……”
女人们就是一朵花儿,女人的生理决定了她对家庭的贡献。
所以我主张女人到了中年要想透点,多几个“家庭维持会”,少一点意气用事,更不要草率的离婚。
是啊,我也知道这说说容易做做难,一时的宽容是不难的,难就难在永远的宽容……这会是种“ 苦刑,“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你说是吧……
新鲜!她的观点我还真没听说过。说得实在,不虚假,是她的经验之谈。因了她的经历她是有发言权的。
三个离了婚的中年妇女,三个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她们从三个侧面勾画出了她们的生存状态。
女性和男性一样,同样会有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宿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有时为为了这种需要而舍弃了那种需要,但需要却是永远存在的。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 沪ICP备11026210号-1
版权所有 ©深秋小屋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13154293@qq.com ladyscn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