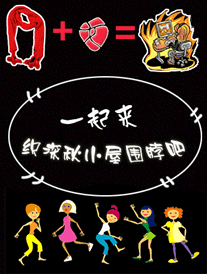【 2005-09-09 10:30:19 编辑:kklk 字体: 大|中|小】
据了解,《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是复旦大学为研究生新设的一门课程。这在中国高校中,史无前例。而这门课,据传也成为复旦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向校党委书记征询报批意见的课。最先构思在大学里开设这门研究课程的,是2003年香港十大杰出青年获得者杜聪。杜聪说,“我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亲身感受到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来自于误解和无知,而目前还没有哪家大学以同性恋本身为中心,从不同角度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后来我遇到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高燕宁老师,和他提起此事,他也非常感兴趣。”
复旦这门课程的诞生可谓来之不易,研究生院对此态度谨慎,并专门向各方征求意见。校内也颇有争议。适时,复旦大学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邱晓露副教授对其他老师说:“同性恋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我们开设这门课,不是从猎奇的角度,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帮助同学们去正视它。应该开。”最终,赞成的意见成了主流力量。在美国,类似《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这种课程早已见怪不怪,许多学生能够公开表明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并且在校园如常的生活行动。
孙中欣对于课程的盛况感到十分惊讶,她对《纽约时报》记者说,“在中国,人们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正在改变。这是很好的过程,但是我仍然感到心情沉重。虽然这么多学生前来听课,但是这让我感觉到正是因为这个话题在以前几乎从来没有被触及过。不仅仅是同性恋们被关在柜橱里,就连这个话题本身也被禁闭了。”据科学调查,同性恋者的比例约占总人口的3到5%左右,这就意味着,在中国至少有3000万左右的同性恋者,而海外的统计则显示,这个数字是4800万。
谁也不知道上海目前有多少同性恋者。“我们是人群中的少数,但只要我们每个人举起手,那将是一片森林!”一位同性恋者这样描述他们的存在。但是,直到1997年,中国新《刑法》才删除了过去常常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恋性行为的“流氓罪”。而到2001年4月20日,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才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实现了中国同性恋非病理化。比美国晚了19年,比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名单上删除晚了7年,被视作重大的突破。
中国重庆的同性恋组织负责人周盛剑(Zhou Shengjian)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许多年来,中国的同性恋者徘徊在社会的边缘,被认为是异见分子。复旦的这门课程,吸引了这么多学生和学者,无疑能够对社会上广大同性恋的生活状况产生正面的影响,同时也有助于和爱滋病作战。”这些同性恋的积极分子期待着类似复旦的课程可以在其它大学也得到设立,从而改善校园内同性恋的生活质量,他们不必再隐藏担忧,甚至可以发起更大规模的争取权益的运动。
同性恋的呼声目前仍然微弱,他们没有法律的保障,同性伴侣在福利待遇、遗产继承与子女监护方面,仍然处于不利的地位。不过,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争取权益的平台,有至少300家服务器在中国的网站关注着同性恋者、特别是同性爱滋病患者的利益。为了防止爱滋病蔓延,中国在19个省建立了42个行为监测点。一些省市也开始为男同性恋者进行血液检查和提供免费的安全套和爱滋病及性病防治资料。中国的卫生部门在男同性恋者聚集的酒吧、公园、公众澡堂和网吧进行调查。
在同性恋者眼里,爱滋更像是一个随时准备出击的敌人。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尽管性取向不同与爱滋完全没有直接关系,但外界已经把同性恋和爱滋病人在某种程度上划了等号。据了解,截至2001年底,加拿大共发现18026宗爱滋病例,其中77.9%的男性患者都是同性恋者;在美国,73%的爱滋病人是同性或双性恋的男性。不过,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董永坤对“同性恋跟AIDS是近邻”的说法进行了辟谣:“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发病率高的结论,是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有关机构调查的结果。在中国,还没有详细资料证明这个说法。”
除了疾病的威胁以外,中国同性恋者还受到难以想象的社会压力。专家指出,让同性恋者得到社会的认可非常重要,从而使他们走出压抑甚至心理畸形变态的阴影。《纽约时报》披露,中国同性恋网站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尽管某些侧重在人权斗争方面的已经被政府关闭,但其它的网站则得以保存。它们有的为会员提供描写同性爱场面小说的下载,有的则为浏览者提供交流的机会。其中最著名的一家网站名为广同,在该站可以找到所有同性恋酒吧和聚会场所的信息,甚至包括海外的地址。
1997年,北京同志热线成立,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完全由同性恋者组成的干预小组,涉及心理健康和AIDS防治等方面。青岛、哈尔滨、大连、西安等城市,也纷纷设立了同性恋热线。2005年4月,上海市同心热线正式开通。在上海市生殖保健指导中心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办公室墙上,志愿者们张贴了同心热线的宗旨,其中写着:“在同性恋群体中宣传和普及性病和艾滋病防治知识”。40岁的北京同志热线志愿工作者李政告诉《纽约时报》,“在中国的每个省会都有至少一个爱滋病防治中心。不过,爱滋病并非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只是借用这个话题走到一起,并希望和社会探讨我们的生存状态。”
但是变革是缓慢的,社会、特别的家庭的承受力仍然非常有限。曾经接受过美国《时代周刊》专访的律师周丹就无奈的表示,当他告知父母自己的性取向时,引发了一场“家庭地震”。复旦大学的学生王谢雨(音译,Wang Xieyu)说,“如果你告诉你的家长你有个男朋友,这也许还可以过关。但是,你还是要结婚,父母有他们自己的考虑,他们要向朋友们交代,要保持家族的声誉。中国现在就如同美国的60年代一样。”来自大连的杨姓女同性恋者透露,她直到结婚后才发现自己的性取向,那年她36岁,和同事发生了性关系。因为有人常常在背后对她们两个指指点点,因此杨现在已经避免在公共场合和她的女伴侣接触了。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 沪ICP备11026210号-1
版权所有 ©深秋小屋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13154293@qq.com ladyscn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