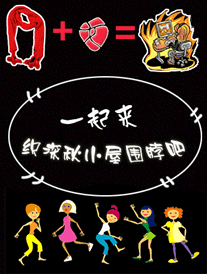【 2005-09-07 10:57:50 编辑:kklk 字体: 大|中|小】
20世纪90年代后的女性在经历了长久压抑和沉默之后,女性言说突破了以往对道德及女性价值的诉求。女性言说在拓展文学领域、重建现代文明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由于女性文学迫切的言说欲望和激烈的反叛情绪,使某些女性文学过于偏激和情绪化,暴露了女性的弱点与女性文学的不成熟,它不利于女性文学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地认识女性言说的误区。
误区之一:与男人为敌。90年代后的女性文学意在瓦解男权文化和男权话语,与男性为敌成为女性文学一个较为普遍的创作思想和策略,这在女性文学创立的初期使女性文学达到了脱颖而出、凸显自我的目的。但随着女性文学的发展与深化,则暴露了它的不足。女性文学始终没有把男权文化和男权话语纳入自己的艺术视野,站在较高的层面审视它、否定它,一些女性写作将其文学的价值体系构筑在敌视男性、蔑视男性甚至虐待男性、压迫男性的“勇敢”行为之上,这种极端化倒置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不理智的脆弱的方式。
合理的途径与策略应该是站在鲜明的女性立场上,书写女性生命的活力,揭示女性的价值,展示女性的魅力,表达女性的生活愿望和精神渴求,以及女性痛苦沉重的付出。以不动声色的言说写出最真实动人的女性形象,以宽容大度的胸怀面对男性世界,以女性特有的魅力,以生命的热力和深沉的爱影响世界、感染世界,在美好中孕育文明、在文明中呈现美好,并由此引领出潮流。如果男性社会与女性社会都各自以自己的优势为依据为对方设置规则的话,那么谁的路都不可能通畅。男性与女性应发挥优势,达到互补,这种互补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与和谐,女性文学的创作意图和批评导向亦应如此,应该建立一个和谐弹性的文学空间和文学视界。这才是女性文学应有的风度、境界和追求。
误区之二:逃避现实。女性文学在90年代曾较为普遍地表现了女性的“房间”意识,即处境艰难的当代女性在本能的内在渴望的驱使下,逃离充满男性霸权特征的外部世界,隐遁于自己的“房间”,求得心灵的安宁和精神的慰藉,以此表达对男性世界的绝望。林白的《说吧,房间》,翟永明的《黑房间》,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唐亚平的《自白》等,都表现了女主人公对“房间”的极度迷恋。由于这些女人躲进了“房间”,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她们的自我封闭,这样使最初的女人与男人之间的战争终于演变成女人的“一个人的战争”(林白)。当“战争”变为“一个人的战争”的时候,与缴械投降无异。这种做法实则放弃了女人的社会权利,否认了女性的社会性,是作茧自缚的文学。女性文学应显示出女性存在的价值,以女性的柔韧与坚强,以敏感细腻的女性触觉对抗男权世界,扬长避短,以柔克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这个世界逐渐达到调和的理想境界。
误区之三:身体写作。90年代后的女性写作出于对男权话语下概念化女性形象的反动,而走向私密化、纯个人化。其突出表现为女性身体经验的深度描写。有相当数量的女性文学作品以一种前卫态度,将某些女性的身体经验像稀有文物一样发掘出来,公之于众。这种极端叛逆,这种类似于自杀式的激烈方式,由于在叙述上过于感性化而往往近于发泄、堕落和自暴自弃,有损于女性形象,这种写作方式也导致女性文学在意识层面的诉求退居次要地位,几乎被毫无节制的身体写作所淹没。决绝并不等于无道德规范,叛逆也不等于放弃与放肆,因为,女性文学也是文学,它是艺术的载体,不是欲望大全。
误区之四:小我意识。女性文学为了突显自我的存在,往往把自我从大我即社会人的身份中剥离出来,远离社会。以向内的视线,将目光锁定在自我的生存范围之内,书写女性的情欲、孕育、家庭、生死、逃离等。这种内视性的写作有明显的不足,这是对女性文学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女性文学的题材和视角都不应局限在女性生活的小圈子里。内视性削弱了女性文学的力量,使女性文学缺乏社会的张力,因为无论男人或女人都是社会的人,女性的自我确认并不是以女权主义为缘起的女性文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女性的社会确认才是它更加理想的目标。因此女性文学的写作视阈应该由自我扩展到社会,将敏感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或从自我出发辐射到整个社会,以自我书写社会、反射社会,用更加积极的写作态度,直面社会人生,以其由此带来的女性意识的客观性、全面性和强烈性震撼读者、打动人心,更能“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样,对女性对文学都将会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女性意识本身也是一个很模糊很宽泛的概念,几乎没有一个女性文学作家能够揭示出:我的女性意识究竟是什么?我们只看到她们对女性历史困境和现实困境的描绘,这很像新时期初始的“伤痕文学”潮流,虽来势汹涌,但毕竟只是对历史创伤的一种表面化叙述,不如后来的文学潮流显得深沉、活泼、富于冲击力。女性意识是什么?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精神或欲望诉求?也许是女性文学作家们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与以往的女性文学相比,我们明显地看到90年代后女性文学的成长,但是从总体上看仍处于初级阶段,表现出对西方女权主义的盲从和图解式的叙述,缺乏中国女性文学的本土性与现实。其中,明显的自恋倾向更暴露了女性文学的狭隘与极端。要想使中国女性文学走向成熟,走向深化和大气,还需要女性主义文学家和批评家付出更多的努力。
上海市通信管理局 沪ICP备11026210号-1
版权所有 ©深秋小屋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13154293@qq.com ladyscn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